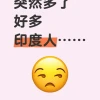中国超级计算机进化史
中国超级计算机是如何实现从无到有,从大型机到巨型机进化的?1950年3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一封书信,信中说“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信的作者是刚从美国经香港抵达北京的数学家华罗庚,这是他在归国途中所书写,目的是号召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文/王剑
1
信中,华罗庚喊出了那一句振聋发聩的话:“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是有自己的祖国的”。
“梁园虽好”出自汉代司马相如辞别梁孝王时的一句感慨,展示了司马相如志在四方的远大抱负。
那时,有很多中国科学家为躲避战火远赴欧美国家落脚,潜心科研,受到了优待。
华罗庚就已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聘为教授,待遇丰厚。
在新中国的号召下,包括华罗庚在内的很多科学家毅然选择从海外辗转回到祖国。
回来后,华罗庚回到清华园,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
1952年夏,有感于美国正开展电子管计算机的研究,华罗庚提倡并牵头,与闵乃大、夏培肃和王传英等人在中科院数学所内,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
那时,中国计算机领域荒芜一片,前行者正高举火把探索未知之境。
闵乃大写出中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研究的设想和规划”,揭开我国电子计算机研制的序幕。
1956年3月,在新中国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中,计算机成为发展科学技术的“四项紧急措施”之一。

同一时间,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研制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同时派人向“老大哥”苏联取经。
1958年,在“立足国内先仿制,后自行设计”的原则下,中国仿制苏联M-3大型计算机的103机研发成功,每秒运算速度1500次,实现了从零到一的跨越。
虽说中国的计算机研发距离美国发明世界首台计算ENIAC,只相差12年,但彼此在人才和设备上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距离。
美国从二战时期就已经展开了计算机研究,从军方到民间有数十万名经验丰富的科研人员,而且经费充足。
中国这时别说计算机研究,很多人连计算机是什么都没搞清楚,更没亲眼见过,经费更是捉襟见肘。
彼时,美国IBM公司在贝尔实验室的帮助下,成功研发出晶体管构造的计算机RCA501型。
由于采用晶体管逻辑元件及快速磁芯存储器,RCA501型计算机的计算速度从每秒5000次提高到几十万次,主存储器的存储量也从几千KB提高到十万KB以上,同时也出现了简单的采用高级语言及其编译程序的操作系统。
与传统电子管计算机相比,晶体管不仅能实现电子管的功能,而且具有尺寸小、重量轻、效率高、功耗低等优点,使计算机体积从过去占满一间房,浓缩为只有一张书桌大小。

1959年,中国仿制苏联БЭCM-Ⅱ计算机研发出104机,速度勉强达到1万次,但是由于组装了4200个电子管、4000个二极管,占地超过400平方。
104机在交付航天与军工部门后,完成了包括第一颗原子弹在内的多项科研运算工作。
虽然104机性能与美国的RCA501型计算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却与同期起步的英国、日本等计算机水平相差无几。
2
面对人才紧缺的问题,中国计算所筹委会与国内多家著名高校合作,连续举办了四期计算机培训班,先后培养出七百多名计算机方面的科研人员,奠定了中国计算机事业的人才基础。
莽荒时代,这支渺小的队伍,如同长夜中微弱的荧光点亮了中国的计算机事业。
中苏“蜜月”结束后,苏联撤走了所有对华援助,其中也包括计算机方面的专家和设备。
中国的计算机科研人员并没有止步,在动乱年代靠集体智慧和奉献精神不断披荆斩棘。

1960年,夏培肃带领团队成功研发出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小型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107机,并交付给当时尚在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使用,这也是我国高校的第一台科研计算机。
1964年,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大型通用数字电子管计算机119机面世;同年,复旦研发出采用机器语言编程的602型电子数字计算机。
1965年6月,中科院计算所成功研发出运算速度定点运算9万次/s、浮点运算6万次/s的首台晶体管计算机109乙机。
随后的109丙机在“两弹”试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功勋机”。
整个六十年代,由于国内计算机研发都是围绕重大国防工程进行,只追求不断提高运算速度,对计算机整体性能和普及性考虑并不多,不仅资金花费巨大,也忽视了社会生产建设需求,更没有批量生产的概念。
进入七十年代,美国以及西方等发达国家已研发出小型化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并广泛在民间开始推广应用。
因此,1973年元月,第四机械工业部在北京召开“电子计算机首次专业会议(7301会议)”,明确未来“必须放弃单纯追求提高运算速度的技术政策,确定发展系列机的方针”。
这次会议后,中国开始了随后近十年的计算机工业发展雏形。
遍地红旗与喧闹的锣鼓声中,中国计算机科研者们一边为经济建设勾勒所需的计算机型号,一边加紧研发。
1973年8月,我国首台百万次集成电路大型计算机150机诞生,这台计算机主内存130K。配有多个程序和操作系统,每秒运算速度达100万次。
从这时起,中国大型计算机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层面,在中国石油勘探、气象预报、科学计算等领域肩负起新使命。

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定型生产的DJS-131计算机,是一台内存4~32K(可扩展至64K)、运算速度每秒50万次的桌面型计算机。
DJS-131小型计算机总计生产了334台,却是当时国内应用面最广、系统最稳定的国产数字电子计算机,被同时应用在23个省市的邮电、电力、铁路、通信、医疗、地震、科研、交通、工业和国防建设等领域。
与此同时,华北计算所组织全国57个单位联合进行DJS-200系列计算机,以及DJS-180超级小型机的开发和设计,开启了微型计算机国产化的序幕。
随后相继出现的NCI-2780超级小型机、TJ-2000系列机及AP数组处理机等产品,逐渐让中国计算机工业走上系列化的批量生产道路。
始终坚持“两条腿走路”,中国计算机工业在小型化和大型化道路上继续保持着喜人的成绩。
1976年11月,中科院计算所研制成功每秒运算速度达1000万次的大型通用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013机,随即广泛应用在航天、国防建设等领域。
参与这些项目研发的,都是当年中国计算所培训班走出的学员。
曾经飘摇的火种,终成科学谱系,在中国计算机各个应用领域散开枝蔓,开启传承。
3
通过自主研发,中国计算机工业已完成了第二代向第三代的过渡,尤其是通过应用促进计算机研制发展,产用结合,推动了微型机的国产化。
虽说中国在大型计算机领域一直坚持不懈进行研发,可与美国还是有着不小的技术差距。
美国从六十年代初就已开发出以集成电路(IC)为主体的第三代计算机,开始了商业化进程。
其中IBM公司发布IBM 360系统大型计算机已可以同时运行许多不同的程序,并向文字处理和图形处理领域延伸,大型计算机更是领先中国许多倍。
拿当时中国比较先进的104机举例,这台后来参与了多个大型国防科研项目的大型计算机,每秒可完成1万次浮点运算;而同期IBM为美国军方设计的7030机,浮点运算性能是每秒60万次。
浮点运算性能的高低决定了科研效率和计算准确性,中国曾尝试花费700多万美元购买,但由于特殊历史环境下,未能如愿。
即便是小型机领域,美国也先行一大步。
七十年代,美国通过DEC的小型机PDP-11开始尝试使用Unix和C语言进行程序设计,满足各种场景需要,真正让计算机步入到“为人民服务”的阶段。
而那时中国的大型计算机无论性能还是产量都还难以满足各种建设需求,尚在艰难跋涉中。
1976年,美国克雷公司又推出了世界上首台运算速度达每秒2.5亿次的超级计算机。
“大型计算机”和“超级计算机”看似差不多,但两者有着天壤之别。
简单说,大型计算机使用专门的指令系统和操作系统,由于只能进行非数值计算(数据处理),应用范围一般局限在商业领域;而超级计算机采用通用处理器及UNIX或类UNIX操作系统,擅长数值计算(科学计算),可以广泛应用于国防、航天、气象、工业等更为尖端和复杂的场景。
超级计算机是真正的“国之重器”,其中汇集了千万计的处理器,能进行海量的数据高速运算,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更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面对现实差距,中方政府决定通过购买设备,从而学习和掌握超级计算机前沿技术的政策。

中美开始恢复接触后,美国为了表示友好向中国出口了两台超级计算机,却让中国计算机科研人员经历了一段屈辱的“玻璃房”的历史。
1976年底,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福特签发了两台Cyber172型超级计算机的对华出口协议。
但美方对这款计算机做了手脚,运算性能远非实际水平,而且美方还要求计算机只能用于地质勘探,不可以用于其他途径。
最令中国科技人员深感愤怒又无奈的是,计算机被设置在专门的玻璃机房内,钥匙却由美方管理,每次使用前,还必须有美国人批准同意。
操作完成后,美方会马上封锁玻璃房,操作日志还要定期上交给美国政府审查。
引进美国的Cyber172后,中方又从日本购入3台日立M系列超级计算机用于气象预报工作。
可美方从中搞鬼,不仅要求日方在对华出口版本上大幅降低性能,还要求比照Cyber172的做法,设立值班人员和监控日志审核制度。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初,中国从美国购买了各种类型的大型和超级计算机设备,关键技术始终被对方严密封锁。
对中国的计算机科研人员来说,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中国科学院院士、前国防科技大学校长杨学军谈起这段历史时说:“这是中国科研工作者心中永远的痛,就像农民自家没粮,母亲自己没奶喂孩子…….”
一而再的“卡脖子”刺激下,中国计算机的科研人员意识到试图通过购买国外先进设备来达到自我提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自力更生才是唯一出路。
4
1978年3月:邓小平听取计算机发展汇报,明确由国防科工委系统承担首台亿次超级计算机的研制,说“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不能没有巨型机(超级计算机)”。
同年5月,中国超级计算机方案论证会上,这项工程被命名为“785超级计算机”,时任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上将取名为“银河”。
“银河”计算机规划性能为每秒1亿次浮点运算,比中国此前研制过的最先进计算机还要快100倍。
接受任务的长沙工学院(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年过花甲的慈云桂立下军令状“就是豁出我这条老命,也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巨型机搞出来!”
慈云桂是中国计算机界的一代宗师。从电子管计算机到晶体管计算机,再到集成电路计算机,中国计算机每一次升级换代,他都是主要参与者。
785超级计算机项目组也表态:每秒一亿次,一次不少!六年时间,一天不拖!预算经费,一分不超!
有委屈可以倾诉,有困难必须克服,实现大国科技实力的崛起,终究要靠一代人不懈的努力。
科研团队首先参考了美国最先进的超级计算机Cray-1总体架构,随后开始了分工协作。国内有配套的设备直接使用,无法实现自主研发的,就从零部件出口条件宽松的国家直接引进。
但是团队有个一个基本原则:设备可以用其他国家的,技术必须是自己的。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科研人员在堆成小山的试验纸带里逐一核对;为了保证机器的稳定和可靠,要对2.5万条绕接线、12万个绕接点和200多万个焊点进行细致检查。
最终,慈云桂团队通过创造性地提出“双向量阵列”结构,大大提高了机器的运算速度,提前1年实现规划研制任务。

1983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台亿次超级计算机“银河一号”通过国家技术鉴定,横空出世。
“银河一号”是中国高速计算机研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个能独立设计和制造超级计算机的国家。
庆功会后,每位研发骨干人员发了五百元奖金,可他们都没有要,全部捐给了正在从事的计算机项目中。
令人惋惜的是,在“银河”系列后续近20年研发过程中,由于工作强度高,营养和医疗条件不足,团队里有许多人因病相继离世。
这些科研人员知道研究经费有限,自己工资也很微薄。为了不给研发添麻烦,纷纷选择了隐瞒病情,一拖再拖。
他们是49岁的钟士熙教授、43岁的蹇贤福副教授、41岁的王育民副研究员、40岁的张树生讲师和35岁俞午龙助理研究员,他们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这些科研人员的遗物里,都有本美国作家阿尔文·托夫勒的著作《第三次浪潮》,书中最后一句话被许多人用红蓝铅笔重重画了一条线,“就像革命的先辈一样,我们的使命注定是创造未来”。
时光在此鞠躬致敬,天下重器,国士无双。
5
“银河一号”出现的同一年,26键方案的“五笔字型”诞生,这是后来蜚声海内外的五笔字型输入法的首个版本,发明人王永民由此被称为现代“毕升”。
“五笔输入”搭配国产D-2000型汉字智能终端及ZD-1110型字符显示终端,古老的文字与代表现代科技的计算机系统,就此相遇。那些跳动字符碰撞成句,连缀成文,在屏幕中演绎属于中国人的文化世界。
这年,中国第一台大型向量计算机系统757机也研发成功,向量运算达到每秒1000万次、标量运算速度每秒280万次。

中国科研机构也用上了电子部六所研发的微型计算机长城100(DJS-0520微机),这台机器已经初步具备了个人电脑的主要使用特征。
窗外已是信息化的世界,“第三次浪潮”席卷而来,人类社会翻开了新的篇章。
在IBM的PC兼容机成为世界主流个人计算机背景下,中国计算机行业提出“照着IBM的PC做”。
只是这种“照着做”实际一没实物,二没图纸,完全靠计算机厂家自行摸索。最终“摸”出来的计算机大多不伦不类,无论性能还是操作系统都无法实现批量生产。
1984年2月16日,邓小平在上海举办的全国十年科技成果展上,摸着一个计算机小选手的头,语气坚定地说“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
老人的叮嘱让计算机课程如井喷,很多学校纷纷开设计算机课程,从简单的打字练习到高级的Basic编程,如火种般点燃了国人学习计算机的热情。
人们在键盘上弹指如飞,犹如在倾诉一个奋进时代的急迫心声。
1985年,中国人通过加载汉化操作系统的国产微机长城0520CH,真正实现了在计算机上进行完整中文信息处理的需求。
同年,销售联想汉卡的计算机公司改名为联想公司。
在长城、联想等品牌带动下,国内涌现出一大批计算机制造企业,如四通、方正、同创、实达等,成为带动中国计算机产业发展的龙头,让中国计算机工业从第三代迈入到第四代。
这是一段浓墨重彩的历史,但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计算机工业一个令人惋惜的停滞时期。
随着中美关系逐渐火热,很多先进技术可以顺利引进。因此,我国计算机和半导体电子工业的发展模式从“创新为主,引进为辅”和重视基础研究,转变为单纯的引进,放弃了半导体通用电路研发追赶计划。
原本与世界差距并不大的集成电路与半导体行业由于没有经费而暂停,大量科研队伍解散,甚至有些研究员被安排当了机房管理员,无所适从。
事实上,我国那时已经可以仿造出6800、8080等CPU芯片,在技术上并不输于很多发达国家。
可由于项目经费缩水,以及研发方向的错失,没能将CPU研究独立出来持续进行,从而为日后计算机的芯片产业埋下了隐患。
幸好在中国科学界有部分专家已经意识到自身与国际前沿科技的差距,不断呼吁,这才使中国超级计算机工程以更快的速度迎头赶上。
6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基于美国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背后蕴藏的强大科技实力,提出要追赶世界高新技术的建议。

邓小平对该建议表示了支持,不久,“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出炉。因为四位科学家上书和邓小平同志批复时间都是1986年3月,所以该计划又称之为“863计划”。
一年后,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内,中国人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从那刻起,中国和世界已经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863计划中,“智能计算机”被单独列为一个主题项目(即306主题),由中科院计算所承接项目。
中科院计算所是中国计算机发展的摇篮,这里诞生了首台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以及首枚通用CPU芯片,是“两弹一星”成功的重要幕后功臣。
当时世界刚掀起人工智能的热潮,日本的“五代机”在这领域发展迅速。因此“306主题”便跟随日本“五代机”的策略,开始了智能计算机的研究。
研发过程中,专家们发现日本的“五代机”主要目标是实现自然语言翻译,但应用市场狭窄,且维护费用高昂。而同时期的美国研发对象是个人计算机、超级计算机和互联网,前景似乎更为广阔。
时不我待,专家组果断把研究方向从“智能计算机”调整为“高性能并行计算机系统”,催生了中国超级计算机系列的加速发展。
负责智能计算机项目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李国杰教授,他意识到当时国产计算机研发几乎都是“闭门造车”,研发时间又极其漫长,往往机器研制出来就已经落后,始终慢市场一步。
于是,李国杰派了团队人员到美国硅谷“洋插队”,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同步更新到项目中。并且,他还在原来的UNIX源代码的基础上,研发设计了国产操作系统SNIX。

1993年10月,峰值运算速度达每秒6.4亿次,采用全对称共享存储多处理结构的“曙光一号”超级计算机诞生。整体与Intel公司1990年的体系结构与技术相近。
随后的曙光1000型超级计算机也开始了市场化运作,进入到企业服务的行列。
1997年,随着曙光天潮1000A落户辽河油田,中国超级计算机彻底打破了进口产品的市场垄断,洗刷了昔日超算领域的“玻璃房”耻辱。
这一时期,随着国产电脑品牌不断涌现,曾经动辄数万元一台的个人电脑价格已经跌到万元之内,普及到寻常百姓家,信息时代的大门正式向中国人敞开。
7
跨越新千年之后的二十年间,伴随国力复苏和科研布局,中国超级计算机研究机构你追我赶,发展如火如荼。
2008年,中科院的曙光5000型超级计算机研发成功,运算速度达超百万亿次。

仅仅一年后,国防科技大学“天河一号”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出现,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个成功研制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的国家。
2010年6月,中国中科院“星云”千万亿次计算机在第三十五届超级计算机TOP500排行榜荣获第二名的佳绩,成功挤入世界超级计算机前三甲行列。
半年后,国防科技大学“天河-1A”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直接夺取排行榜的第一名。
与此同时,江南计算机研究所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神威·蓝光”,率先完成CPU国产化。
在中国超级计算的赛道上,曙光、天河与神威已成为高性能计算专项课题耀眼的“三剑客”。
随着超级计算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相继建设了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深圳中心、无锡中心、郑州中心等7家机构。
在此期间,基于超算体系结构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创新也在不断上演新的篇章。
2018年,曙光、天河与神威已进入到超级计算机竞赛领域的E级(秒钟运算一百亿亿次)超算研发,并逐步实现CPU和加速器的全国产化。
2021年,第五十八届全球超级计算机TOP500排行榜中,中国超级计算机有173台进入榜单,占比34.6%。第二名的美国为149台,占比29.8%。
不过,中国超级计算机数量虽然超过了美国,但在综合算力上与美国及其他国家依然有一定的差距。

2022年上半年的全球超算TOP500榜单中,中国的神威太湖之光排名第六,已是“三剑客”中成绩最好的一家。
但是距离全球首款E级超级计算机,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边界超级计算机(Frontier),在算力上尚有10倍左右的差距。
可以说,中国的超算体系面前,变局从未止步。
上世纪六十年代,英特尔创始人之一的戈登·摩尔预测,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目,未来将以每18个月翻一番的速度稳定增长,并在今后数十年内保持这种势头。
摩尔定律从此成为时代的法则,更成为人们对未知世界的一个进化隐喻。
中国的超级计算机从荒芜走到沃野,已在千古棋局行至中盘,在时代变局中日渐清晰,凝聚起磅礴的力量。
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说:凡是过往,皆是序章。
中国超级计算机的前方是瞬息万变的数字化浪潮,但落子无悔,胜负依然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