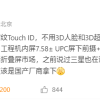中国造芯往事:热钱是最不重要的
一年前,同样是在5月,一场突如其来的解散会议,让OPPO旗下芯片研发公司“哲库科技”站上了舆论的焦点。哲库的失败不仅让3000多名从业者一夜之间失业,职业生涯甚至人生轨迹都被改变,更是给中国高端芯片研发蒙上了一层阴霾。
哲库解散事件,是国内高端芯片行业这几年来动荡的一个缩影。2018年以来,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高端芯片创业浪潮涌来,滚动着的热钱,和一大批怀揣财富梦想和家国情怀的人,都一股脑扎入这个数十年如一日的传统行业。
直到浪潮逐渐退去,身陷其中的人们才发现,钱并不总是万能的。风口、融资、红利,这些现代商业的逻辑,在芯片这个古老的行业里失效了。也许,这从来就不是需要奇迹的行业,热闹过后,中国的高端芯片,需要更多的耐心与时间。
无人意料的结局
再次被丢进茫茫的招聘人海时,年轻的王伟安起初还抱有幻想,“工作没有了,就再找一份,反正也不是只有自己被裁了”。他曾是OPPO旗下芯片设计公司哲库科技的一名芯片设计工程师,2023年5月12日,OPPO宣布关停哲库所有业务,包括王伟安在内的三千多人的团队,一夜之间被解散了。
这个1997年出生的年轻人善于汲取教训,对下一份工作的目标非常明确,“公司要以稳定为主”,钱的来源是最主要的衡量指标,“要看是融资还是国家控股”。
现实的冷水一再泼来。投出去几十份简历,“有消息就算回复的话”,得到回应的不到一半,里面还有超过1/3是拒信。好不容易得来的面试机会,也一再让他感到挫败,“专业的问题你回答不上来,心里就有数了”。
聊起在就业市场上受挫的原因,王伟安直截了当:“因为我没有竞争力。”
就在一年之前,王伟安还是令同龄人仰慕的芯片工程师:某C9院校集成电路专业硕士,毕业时就揣着40万年薪,一脚踏进哲库这个芯片“新星”企业。
短短一年时间,那份曾让他引以为傲的工作,却成了找新工作的阻碍。它让王伟安失去应届生的身份优势,但却没有给予他足够的成长周期——大部分企业都要求三年工作经验,简历上的王伟安仅有一年工作经验,作为一个备受瞩目的项目中的边缘成员,而这个项目甚至还谈不上成功。
“像我们这种刚入职一两年的小白,没有猎头愿意找我们。”王伟安说。
他并没有气馁,在遇冷的就业市场上,一步一步降低标准和预期。最先被划掉的是公司的规模和体量,“不论公司大小,肯定有可以学到的东西”。紧接着是薪酬,他说自己心态还算平和,“一开始我说平薪就好”。但显然,他的乐观还是超出现实,市面上,几乎没有一家企业愿意以同样的薪资接住这样一个新人工程师。
时间越来越紧迫,最后王伟安不得不妥协,“只能通过降薪来提高竞争力”。
这样的情形,放在一年之前简直不可想象。2022年秋招时,科班毕业的王伟安找工作几乎没有难度,“只要是科班,有项目能拿得出手,offer真是拿到手软”。那个时候,十几份offer摆在王伟安的面前,平均薪资能比往年高出25%。
王伟安不是喜欢追赶浪潮的人,他曾敏锐地感知到35岁危机和时代、行业红利带来的陷阱,高考结束后便开始布局自己的人生。选专业刻意避开互联网,“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下滑的趋势,网传说35岁当不了领导就会被裁员”。
在综合考虑了生活的城市,以及企业的规模、赛道和资金来源后,他最终选择了哲库,“所有项目加一起有3000多人,感觉比较稳定,又是OPPO全资子公司,不愁融不来钱”。
对于一个尚未涉足社会的年轻人来说,这些考虑已经足够缜密。接下来的时间里,似乎也在印证着这个选择的正确性。入职时,王伟安被送往上海脱产培训一个月,住的是五星级酒店。公司看起来资金雄厚,员工福利充足,有咖啡机和制冰机,还有下午茶,每周还有羽毛球、篮球这类的社团活动和外出团建,逢年过节还能抽奖。
不仅如此,在国内的芯片行业,哲库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这家背靠OPPO,以自研旗舰手机SoC(System on Chips,集成CPU、GPU、通信等模块的手机核心芯片)为目标的芯片设计公司,持续向外界展现它的雄心。
它以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来命名芯片自研计划,来形容做“顶级芯片”这件最难的事情。母公司OPPO为其输血和搭建完整的产业配套。2019年,OPPO连续投资十来家与半导体相关的上下游企业。之后,OPPO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陈明永宣布将投入500亿预算,用于芯片等底层技术的研发。
那是国内芯片企业群雄竞起的时期,行业人才奇缺。为了能尽快让链条滚动起来,哲库以行业最高薪酬水平从华为海思、中联科、紫光展锐等头部企业网罗人才,不到四年的时间便搭建起超过2000人的队伍。根据公开招聘资料,哲库接近80%的工程师来自海内外顶尖高校,拥有超过5年以上的行业经验。
它目标明确。最初便将研发重心放在难度最大的Soc芯片和基带芯片,期待像苹果那样,通过使用自研芯片,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利润和竞争力。王伟安记得,在新人培训会上,公司未来的设想被反复提及,“整个蓝图甚至已经规划到未来几十年后的产品了”。
2021年哲库发布第一颗自研影像专用NPU芯片“马里亚纳X”,可以帮助手机优化拍照效果,宣称一年后OPPO所有旗舰手机都将搭载上这颗自研产品。第二年,哲库推出第二颗蓝牙音频自研芯片“马里亚纳Y”,可以支持蓝牙耳机传输无损音频。这颗芯片采用了N6RF工艺制程,是全球除苹果以外唯一使用这一先进工艺的公司。就在同一年,OPPO投资近45亿的研发中心项目落地东莞交椅湾。
按照计划,在影像和音频芯片后,哲库就要推出手机最核心的Soc芯片。造芯的路看似稳健地向前迈,现实却骤然挥来一棒。2023年5月,因“安全系统升级”,哲库全体成员被要求居家办公,隔天开启线上全员大会,团队直接宣布解散。这颗正在直冲云霄的新星,瞬间坠落,砸落在地的,还包括3000多个员工的饭碗。
从平静到疯狂
哲库解散后,一直到2023年的冬天,芯片的海已经被冻住了。寒气之下,25岁的芯片行业猎头晓然很久都没有谈成一个单子,“收入很惨淡”。企业岗位从几十个下降到个位数,甚至是零,求职者的心态也变成以“稳”为主,“候选人更加谨慎,他们会担心不稳定,选择留在原公司”。
这位入行还不到两年的猎头,从来都是追着风口跑。她先是投身地产和互联网,在行业的黄昏到来之际,又感受到芯片行业吹来的风。在B站上搜索了几个专业视频,记下那些拗口的专业术语,摇身一变,2021年下半年,这个年轻的女孩成为芯片行业的一枚猎头。
遗憾的是,她只抓住了风口的尾巴。她曾听过不少芯片行业曾经的风光,“那个时候真是遍地都可以捡钱”。至今她都遗憾,“我入行时间短,没有行业沉淀,还是迟了一丢丢”。
一脚踩进去,即便是行业小白,也很快被卷进当时疯狂的抢人大战中。根据公开数据,2018年起国内注册在案的芯片企业数量急剧上升,2020年注册在案的芯片企业为59793家,是2014年的近5倍,比10年前增加了近100倍。
为了能迅速地跑马圈地,这些初创企业四处招揽人才。“小公司要融资,肯定要请人来做事”,晓然说,“但是规模小,无法吸引到人,只能靠猎头介绍优势”。它们为此开出高额的猎头费,一个最基础的工程师岗位猎头费能有五、六万,相比之下,大公司仅有高级别的经理和工程师才会给付猎头费,也只有几千块钱。
不仅如此,初创公司的老板甚至亲自下场,专程飞往异地说服候选人。许多猎头干脆绕开流程,只要拿到候选人电话,就往企业的系统里直接录入,先抢占名额,“甚至都还没有联系对方”。
另一端是高高在上的求职者。他们当中不乏有人中途转行,花钱学几个月的速成班,再把简历上传到招聘网站,每天几十个电话一涌而进,手上能同时握着七八份offer。沟通职位时,一位候选人回复,“这家公司的注册资本还没我家存款多”,便把晓然删除了。一家芯片企业的HR回忆,因为沟通offer比预计迟了一天,电话对面的应届生便指责起来,“你怎么这么慢?我们难道不是上帝吗?”
当然,大多数时候,只要给钱足够多,其他都好说。在芯片行业,2021年和2022年的校招几乎是用钱堆起来的。哲库抢人的方法就是钱,在其它企业的薪酬之上,直接double来“掐尖”。行业苦不堪言,但又不得不加入战争,“凭一己之力把整个行业的薪资水平拉高了”,一位手机芯片企业的HR说。
这些看似花不完的钱都是从上游传导下来的。据云岫资本《2020年中国半导体行业投资解读》,2020年半导体行业投资金额超过1400亿元人民币,比2019年增长近4倍。创业公司璧仞科技更是在当年创造了“每3周就融一轮”的“芯片速度”。
投资人Bob对芯片一无所知,也不妨碍他拥抱芯片,“90%以上的半导体投资人知识储备都不及格”。但Bob有自己的一套做事逻辑:前一夜百度专业术语,第二天也能在饭桌上与创业者侃侃而谈,“我要听懂这个词是什么,还要能搭上一句话,显得很懂,一定不能露怯”。
投资逻辑也不算难,在所有公司都没有产品的时候,只能看创始人的背景,“最青睐的就是国外的、比较顶级的半导体公司的工作经历”。
回忆起当时的疯狂,Bob说:“很多人的心态不是怕投错,而是怕错过。”一位在当年坚持不涉足高端芯片的投资人表示,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合伙人,“为什么所有机构都在投而你不投?”
这些疯狂都被王利看在眼里。他是一个芯片设计工程师,2013年毕业后就进入一家通信企业的芯片设计部门工作。风口到来之前,王利的工作朝九晚六,“和公务员差不多”。在他的经历里,尽管芯片制造工艺持续往前推进,但设计领域还比较传统,研发的手段是老的,流程也是固定的,“没有特别新的东西,就像汽车和机械行业一样”。尚未“缺芯”的年代里,芯片自研缺少了许多动机和热情,“大不了买别人的,也挺好的,反正也是白菜价”。
那时,更好的职业选择都是去互联网。王利是被分配到芯片部门的,他只能“既来之,则安之”,有时看到那种企业外包开发App的项目,一个就赚几十万,他也很心动。本来以为自己错过了风口,可没想到,2018年后,芯片突然火起来了,热钱来了,猎头们来了,最夸张的时候,一天有十几二十来个猎头联系他,都是初创公司在招人,有的岗位甚至开出百万年薪,大家都想从“国产替代”里分一杯羹。
行业还是那个行业,但这里的水温已经沸腾了。
钱是最不重要的
王伟安在哲库加入的第一个项目就是马里亚纳Z3。在企业高层的设想里,这颗搭载5G基带的SoC,运用的是台积电最先进的4纳米工艺,将成为哲库第一代顶级芯片,前哲库首构架构师公开称它将是“一颗业界领先水平的SoC芯片”。
这颗被寄予厚望的芯片,驱动着哲库上下三千人的连轴转。在王伟安的印象里,入职之后,所有的部门都在为这颗芯片的流片(试生产)做准备,他每天晚上9点以后才能下班,周末也只能单休。
还是缺人。当时王伟安所在部门领导最大的困扰就是“招不到人”,上层更是直接以下达命令的方式,要求他的部门从原有的二三十人增加到六七十人。作为新人的王伟安,注定只是一个边缘角色,既接触不到核心的工作,还要随时被调配,作为一名设计工程师,他干得最多的是“支援验证”。
不仅人才错配,快速扩张也带来了资源争夺、离职潮以及交付延期等管理难题。来自不同企业背景的人汇合在哲库,衍生出派系争端、行事风格磨合的问题。一位哲库前资深员工在接受采访时提到,经常存在两个部门都在开发同一个功能的现象,“这时候就会出现资源争夺的情况”。
暗流涌动之下,计划看似按着蓝图有序推进。2023年春天,这颗极具开拓性的Soc芯片,漂洋过海,被送往台积电进行流片,也就是进行小规模试生产。
严格意义上来说,一颗真正能被市场接纳的成熟高端芯片,需要漫长的技术积淀。以华为海思为例,从成立到麒麟9系列芯片的问世,历经10来年,最终实现7nm工艺。如今称霸市场的高通骁龙芯片,其技术的起源更得追溯到2G时代。
成立不到四年的时间,哲库却以狂奔的姿态,先后推出高算力影像处理芯片马里亚纳X,以及高速蓝牙处理芯片马里亚纳Y。之后它便跃过技术的基础,向难度最高的5G SoC芯片发起挑战。
这也是哲库被广为诟病的原因之一。在芯片行业里,它的失败似乎没有带来太多的冲击。“意料之中”,芯片设计工程师王利说。在王利看来,哲库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技术基础,一上来就搞这么难的芯片”。
王利解释,技术基础很难用钱堆起来。手机处理器芯片涉及到摄像、图像处理、WIFI等模块和接口,这些都需要一个一个去开发和积累。如果自己开发,它将需要不停地迭代、测试和评估,“这是一个很漫长、很痛苦的过程”。
哲库试图用钱来弥补缺陷,比如高成本挖人,但却很难奏效。芯片的研发过程中,最基础的是设计代码。王利以华为麒麟处理器芯片举例,前端设计涉及几亿行代码,一个简单的文件大小就有几百个G,它们一般都会以加密的方式存储在大型的服务器上,“这些东西你怎么把它弄过来?”
购买IP或许是一条有效的加速路径。这也是国内这一轮芯片自研热当中的“秘诀”。但这也意味着更高成本的投入,“合算起来,这个成本夸张到难以想象”,王利说。“没有技术基础导致所有成本都摊高了,最后肯定维持不下去。”
不仅如此,即便解决技术的积淀问题,依靠资金堆叠而起的这些芯片项目,还需要长达几年的周期验证。以一颗7nm的芯片为例,从诞生到量产,要经历设计、验证、流片、回片后的功能和性能测试等一系列复杂的流程。
按照传统的经验,如果流片一次成功,最快需要一年。现实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在7纳米上一次成功,包括高通”,投资人徐清说。“因为总会有bug,要修复再修复。”
一端是技术缓慢的迭代和累积,另一端是猛然扎进芯片行业的热钱需要迫切的回报。令门外汉们没有想到的是,所谓的风口、融资与红利,在芯片这个古老的行业失效了,热钱在这里跌了一个跟头。
钱是这个行业里最不重要的东西,徐清说,“所以,严格意义上这个事是不可能加速的,不是有钱就可以加速。”
无奈的选择
时钟回拨到2023年,多重冲击在这一年交织袭来。
首先是不乐观的外部输血环境。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智能手机销量下滑12%,OPPO更甚,出货量同比直接下跌27%左右。电子消费寒冬,直接影响了哲库母公司OPPO的输血能力。而严重依赖低端千元机市场的OPPO,与哲库的芯片,出现了需求定位错配的问题。
那么,随着手机产业需求的萎缩,即便未来高端芯片实现量产化,摆在哲库和OPPO面前的问题是,未来商业化的可能性与市场究竟有多大?
很多人开始意识到,造芯之路上,技术的壁垒和周期只是一个开端,更为重要的是,自研芯片之后的商业化难题,还有产业生态的缺失,才是摆在中国高端芯片面前的最大拦路虎。“高端芯片的核心问题是由谁用,怎么用的问题,没人用,它的生态就没法建立。”投资人徐清说。
徐清将高端芯片的生态比喻为“一个金字塔”。他举例,掌握X86架构的英特尔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往下有定义数字化基础结构的技术,微软的操作系统,以及最底层的应用Adobe。显然国内高端芯片缺乏这样的市场生态,这也是“国产化替代”浪潮之下,自研芯片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它是层层递进的,如果连这个金字塔都没有,那做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生态缺失的问题,在高端芯片的上下游链条里,也逐步显露。从EUV光刻机到芯片设计工业软件EDA,技术的密码都掌握在欧美国家,这些都成为芯片自研道路上“卡脖子”的关键环节。每一家试图挑战芯片技术难题的中国公司,都要面临欧美国家的专利封锁和各种限制。
多重因素交织,中国高端芯片行业迎来泥潭深陷的时刻。
哲库的解散,宛如一颗深水炸弹,震动的余波陆续传导开来。2023年8月,星纪魅族集团终止自研芯片业务,11月TCL控股的子公司摩星半导体解散。海浪之下,被掀翻的还有无数条小船。据钛媒体报道,2023年共有1.09万家芯片相关的企业工商注销、吊销,比2022年增长了89.7%。
行业动荡之下,那颗曾经满载着国产替代希望,漂洋过海的马里亚纳Z3,甚至没来得及传回音讯,便已被人遗忘。身处芯片行业的人们正在焦灼地寻找各自的出路。
投资人Bob和猎头晓然黯然离场。“再花五年,我也不可能达到专业的高度,永远只能是一个平庸的三流投资人。”Bob说。在他的感知里,2022年初,身边的半导体投资人陆续开始做投后工作,也就是找人对接资源,提高被投企业的业绩,甚至有的人已经在考虑止损退出的问题了,“这个时候,风向已经变了,不是想着进去,而是想着出来了”。
行业的挫折或许也孕育着新机。热钱退出以后,行业经历洗礼,身处其中的人们开始变得理性起来。趁着行业的风口,一位女孩从材料专业跨行到芯片行业,却很快从风口上摔下。她经历两次被裁,放弃对“稳定”的追求,“不管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基本上都会面临裁员”,在最新的工作机会里,她希望“能学到一点东西,提升自己最重要”,反正“大环境你已经改变不了了。”
离开哲库后的王伟安,最终以平薪的待遇,成为西安一家小型芯片公司的工程师。小公司看起来并不规范,比如项目的进度只能由领导来拍板,相比之下,哲库作为大公司流程完备,也有共享的知识文档。
但他没得挑。“毕竟你不去选择这个机会,下一个机会在哪里就不知道了。”
路过原来在西安的办公楼,王伟安发现,哲库的痕迹已经被抹得一干二净,同一栋楼里,现在备受瞩目的,是同样以自研手机芯片为目标的小米,“我们刚倒了,他们又进去了”。中国高端芯片的研发之路,还得有人继续走下去。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