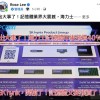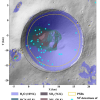气候临界点迫近:不可逆的影响和积极的“转折点”
莱顿喜欢把临界点的到来想象成一个人靠在折叠椅上的状态变化。“当你不断向后倾倒,你会得到一种非常简单的结果——重力将你向后推倒,直到‘啪’的一声。”莱顿说。
2008年,他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ANS)发表了一篇关注“地球气候系统中的临界要素”的论文。这篇后来被许多科学家引用的文章极大推动了临界点领域的研究。当时,他在论文中提出了9个临界点,并根据它们发生的可能性进行了排名。
十多年来,气候临界点这一概念正在引起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今年9月,莱顿教授的团队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布了一项最新研究,重新评估了自2008年以来科学界发表的200多篇关于临界点的论文数据。他们发现,现在全球主要气候临界点可能已经增加到了16个,如亚马孙热带雨林的枯萎、北极海冰面积减少、全球珊瑚礁大规模死亡等等。
莱顿的最新研究指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造成的全球升温已达1.1摄氏度,全球有5个临界点已处于危险区。假使全球升温达到1.5摄氏度,其中4个临界点很可能会被触发乃至越过,同时另外5个临界点将进入危险区;若全球升温达到2摄氏度以上,将触发最后6个临界点。
这项研究发表后,莱顿教授在埃克塞特大学召开了一场研讨会,来自全球各地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和民间社会代表汇聚一堂,不仅带来了他们最新的研究结果和看法,也一起探讨了如何应对全球变暖中“临界点”的前景。
在研讨会开幕式上,莱顿教授说道:“我们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我们强烈地感觉到人类活动正在把地球系统推向破坏性的临界点。我认为,我们避免这些糟糕的临界点的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后的希望是通过在人类社会中发现并触发一些 ‘积极的临界点 ’,这些临界点会改变我们的社会,改变我们与地球系统其他部分的关系。”
就在这场研讨会召开之际,第77届联合国大会也于9月13日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拉开了帷幕。在开幕式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呼吁全球社会关注气候危机。
就在两周前,由世界气象组织 ( WMO ) 协调联合国多个机构发布的一“联合科学”报告显示,尽管近年来有关气候变化的警告越来越多,但各国政府和企业的变化还不够快,其后果已经在世界各地日益极端的天气中显现出来,一些气候临界点可能已经被突破。
正如莱顿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所警示的,“近几年来全球各地的极端天气已经传递出越来越多令人不安的信号——若世界达到气候临界点,我们将面临气候系统不可逆转的变化。”
不过,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瑞典哥德堡大学物理气象学教授却有着不同的观点,“单个气候临界点影响都是区域性的,单个临界点被触发并不等同于全球平均温度的重大改变。”他认为,由于数据和模型的问题,相关结论还有特别大的不确定性,科学家们还要积累更多的研究。

2021年1月,英国南极调查局飞越布伦特冰架时发现的裂缝。
气候临界点是什么?
在研讨会开幕式的全体会议上,莱顿教授用一张动画图形象地描述了地球系统中临界点的概念。
“就像许多复杂的系统一样,这里有两个稳定的状态。(左半边)的图中球从一个盆地中开始运动,盆地的深度代表这种状态的稳定程度。系统的压力导致左侧盆地变得不稳定,球短期内在盆地中被推来推去——类似于气候系统中的极端天气事件。最终,球被推过越来越不稳定的左侧盆地,突然落入另一个盆地。在那里,它处于一种新的稳定状态,并不能轻易从中返回。”莱顿解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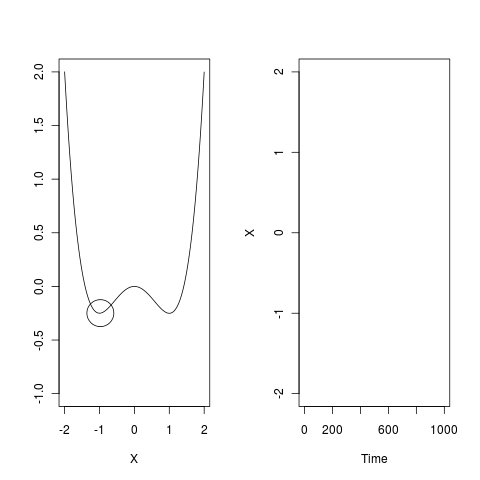
气候临界点概念示意图
事实上,20年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就提出了 “气候临界点” 的概念,并在其官方术语表中给出了其定义 :“就气候系统来说, 临界点(Tipping point)指的是全球或区域气候从一种稳定状态到另外一种稳定状态的关键门槛。”
假使用2018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在其著作《气候赌场》里的比喻来进一步理解气候临界点的概念,那么可以想象一下一叶在水面上漂浮的独木舟,当独木舟倾斜进水的时候,一开始尚可保持平衡,但一旦船体倾斜到一定程度,独木舟就会瞬间倾覆——令独木舟瞬间倾覆的倾斜角就是临界点。
更通俗地说,临界点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关键节点,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莱顿对澎湃新闻表示,临界点变化的关键在于,在一个“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可以自我推进”的系统中,存在着一种“正反馈机制”(postive feedback)。莱顿又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特点。“若一个人听到火警警报,跑向出口,会导致另外两个人逃跑,之后导致四个人逃跑,八个人逃跑,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临界点和 ‘自我推进’的 ‘逃跑反馈’情况。”
长期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上海浦东益科循环科技推广中心项目总监武毅秀告诉澎湃新闻,临界点之所以重要,是由于除了每一个临界点的突破都会对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影响外,还因为其具有两个不可忽视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不可逆性。到达临界点的累积时间可能很长,在这个累积时间段,避免触发临界点的努力是有意义的,而一旦触发临界点,整个系统可能会很快地遭遇坏结果——在临界点之后,系统会进入新的平衡,但不会再是原来的状态。
第二个特点是难以预测性,而这也是其最危险的地方:尽管人们知道危险将会来临,却无法准确预见临界点何时到来。当我们意识到临界点来临时,临界点实际上已经被触发。
莱顿担心的是,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表明,世界已经处于接近可能产生重大、长期、不可逆转影响的临界点的风险之中,甚至一些临界点可能已经被触发。
早在2020年,莱顿的团队就在《自然》杂志发文指出,全球超过一半已被辨识出的气候临界点已呈现出活跃状态,其中几个临界点的到来已经非常迫近。
此次发表的《科学》研究更进一步指出,目前全球升温1.1摄氏度已经将几个临界点推入“可能已越过”范围——其中包括格陵兰岛和南极西部冰盖的崩塌、全球热带珊瑚礁的大规模死亡以及北半球永久冻土层的解冻。
“我们给出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范围,但(一些临界点)肯定处于危险区域 。我们可能正处于一个更大规模触发乃至越过临界点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还没有越过,但是这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可能。”莱顿对澎湃新闻说。
莱顿进一步补充道,最近几年夏天的天气情况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很难将它们作为现有状态的一部分。“也许它暗示着另一种天气状况的存在,这是我的担心。”莱顿说。
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瑞典哥德堡大学物理气象学教授陈德亮未参加上述研究,但身为国际气候专家的他告诉澎湃新闻,莱顿团队研究的意义在于把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对临界点的理解进行了总结,然后放在一起做了一个判断,得出一个结论:大概在什么样的温度下会产生一个重大的变化,临界点将被触发乃至越过。
“不过要指出的是,所有的单个气候临界点影响都是区域性的,单个临界点被触发并不等同于全球平均温度的重大改变,而且由于数据和模型的问题,相关结论还有特别大的不确定性,我们还要积累更多的研究。”陈德亮说。
尽管如此,大多数气候专家都同意,这项研究大致描绘出了我们将在未来面临的最重大的气候变化挑战。

莱顿最新研究显示的全球16个临界点
气候临界点的影响
近年来,全社会对气候临界点会带来的巨大影响的认识已有所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像莱顿一样的科学家们的工作。
莱顿告诉澎湃新闻,当他在2008年发表关于临界点的论文时,预测的某些方面仍然是理论性的。但从那时起,随着气候灾害事件破坏率的增加和科学家观察气候变化能力的提高,临界点的证据得到了加强。在最新发表的研究中,他的团队总共确定了16个临界点,若这些临界点被触发,将产生“深远的区域影响”。
2008年莱顿论文里列出了九个主要临界点,其中的大部分在201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全球升温1.5摄氏度特别报告》里也有提到。
这些临界点包括:(1)亚马孙热带雨林的枯萎;(2)北极海冰面积减少;(3)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AMOC)的减弱;(4)北美的北方森林火灾和虫害;(5)全球珊瑚礁大规模死亡;(6)格陵兰冰盖加速消融失冰; (7)永久冻土层解冻;(8)南极西部冰盖加速消融失冰;(9)南极洲东部冰盖加速消融。

2008年识别出的九个主要气候临界点
事实上,其中一些临界点可能已被触发。莱顿告诉澎湃新闻,过去十年的研究表明,南极洲西部阿蒙森海的冰川消融可能已经突破了临界点 ——各个模型的演进都显示,在这片区域,海洋、陆地和基岩相遇的 “交界线” 正在持续后撤。若南极西部冰川全部融化,可能致使全球海平面在未来数百年到几千年的时间上升约3米。
同样的情况也在北半球格陵兰岛的冰盖发生。相关模型研究表明,格陵兰冰盖融化的临界点在升温1.5℃时就可能被触发。假使格陵兰冰盖全部融化,它会在数千年的时间内使全球海平面上升约7米。
莱顿也同意,研究人员还需要更多的观测数据和时间来确定相关冰盖是否已经达到临界点,但可以肯定的是,南极洲和格陵兰岛的冰盖是地球上“最脆弱”的临界点之一,眼下距离触发两地大规模冰盖消融已 “非常接近”。
若南极西部冰川和格陵兰冰盖融化的临界点被触发,将最终导致全球海平面升高十米,纽约、洛杉矶、圣彼得堡、新奥尔良、上海、爱丁堡等全球各大沿海城市,届时都将被海水淹没而不复存在。
另一个有着巨大威胁的临界点是冻土层的解冻。那里封存着大约相当于当前全球大气中两倍数量的碳。IPCC 报告写到:假使按照当前的升温速度,全球约70%的永久冻土会在本世纪末消融,沉睡在冻土层里的碳一旦被解封,将会持续释放很长一段时间而很难停下来,这将进一步加强温室效应的恶性循环。
亚马孙雨林作为全球最大的热带雨林,是全球十分之一已知物种的栖息地,也是世界最大的储碳、固碳森林。在埃塞克特大学的研讨会上,德国慕尼黑技术大学地球系统建模教授尼克拉斯·布尔斯(Niklas Boers)表示,自2003年以来,由于森林砍伐和气候变化,四分之三的亚马孙雨林已经丧失了“恢复力”。这“可能已将亚马孙地区推向了雨林枯萎的临界点”,进而对南美季风产生连锁影响,减少30%至40%的降水量。
武毅秀告诉澎湃新闻,作为缓解气候变化的得力帮手,亚马孙雨林长期储存的碳大概相当于全人类十年的排放总量。一旦这个临界点被突破,如此高量的碳被释放到大气中,将使全球二氧化碳浓度激增10%。
在海洋方面,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AMOC)是大西洋中的一个主要洋流系统,而它或已经处在千万年来最弱的时候。
德国波茨坦大学海洋物理学教授斯蒂芬·拉姆斯托夫(Stefan Rahmstorf)教授在会议上更进一步表示,“几周前,我看到的一些尚未公布的数据表明,AMOC可能处于过去1170万年来最弱的时期。”
AMOC的进一步减弱可能对欧洲带来巨大的影响,导致更多风暴、更寒冷的冬季以及整个欧洲极端高温热浪和干旱的增加。
也有专家表示,全球珊瑚礁大规模死亡的临界点是最大的担忧,因为这“直接影响到数亿人的生计”,特别是较贫穷的热带地区的居民,他们直接依赖与珊瑚礁有关的渔业为生。
大部分专家都同意,观测证据表明,一些主要的地球系统临界点正在失去稳定性。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所长约翰 · 罗克斯特罗姆(Johan Rockstrom)将其比作在炸弹上点燃导火线,“导火线会燃烧起来,直到大爆炸的发生。”
陈德亮向澎湃新闻表示,“倘若我们对地球系统的运作有很好的理解,那么预测就会更准确。过去发生的(气候事件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加强理解,但模型不能代替未来。眼下发生的许多气候事件是过去从没发生过的,这对于预测未来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近年来更令科学家们担心的是,全球的临界点是相互关联的,一个临界点被突破,可能会增加其他临界点被突破的风险。一旦气候变化的多米诺骨牌被推倒,则全球的级联效应(Global Cascade) 将变得不可避免。若发生这种连锁反应,全球平均气温可能将会上升至高于过去120万年中的任何时期,地球将变成“温室地球”,最终形成对人类生存与文明的威胁。
“大约十年前,我们认为这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现在我们有了更直接的因果关系的证据。”莱顿对澎湃新闻说。
莱顿具体解释道:比如格陵兰冰原融化,会向北大西洋注入大量淡水,进一步减弱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这会减少南半球向北半球输送的热量,把热量留在南半球的海洋,进一步加热南极冰盖的融化。
覆盖两极的白色冰雪原本可以反射太阳光,但若冰雪融化,裸露出的棕色地表和海洋将会吸收更多的太阳热辐射,从而加剧永冻土层的融化,让更多冰雪消融,形成恶性循环。
对此,陈德亮也表示认同,不过他指出,全球范围内不同临界点具体如何互相影响,影响又有多大仍有待进一步的科学研究。

2021年9月11日,位于格陵兰岛努克以南约80公里的塞尔梅克冰川正在融化。
“积极”的转折点
如何应对迫近的气候临界点?在埃克塞特大学的会议上,与会者们发起了一项名为“积极的转折点”(Positive Tipping Point)的倡议 ,期待引发全球社会的快速转变 ,从而及时应对气候危机。
莱顿向澎湃新闻举例解释说,一个“积极的转折点”可能是可再生能源价格的加速下降以及各方对部署这些技术的巨大政治支持。
“我们相信,改变根深蒂固的行为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找到社会和政治的 ‘积极临界点’。我们必须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找到并触发这些积极的临界点,从根本上加速全球经济的脱碳,以限制气候系统中极具破坏性的临界点带来的风险。”
参加埃克塞特大学会议的科学家们强调,现在将资金和注意力转移到迅速扩大零碳排放的可再生能源规模上,仍可以阻止许多灾难性的临界点到来。眼下在许多地方,可再生能源已经和化石燃料一样便宜。大多数主要的汽车和卡车制造商现在都在计划停止生产化石燃料汽车。
英国牛津大学马丁学院(Oxford Martin School)复杂性经济学项目主任多因·法默(Doyne Farmer)在会上表示,未来几十年内可再生能源的成本预计将大幅下降,以至于其它任何能源都将很快失去竞争力。
莱顿以英国为例:“十年前煤炭发电占该国电力的40% ,现在英国计划到2024年停止使用煤炭发电,这就是一个积极的转折点。”
而上述变化是由三件事共同引发的:对风电的投资、在发电行业引入碳定价以及欧盟碳交易。“一旦投资煤炭变得无利可图,企业就会开始拆除燃煤发电站。”莱顿说。
另一方面,公众的意识和参与度仍有待提高。根据调查机构益普索去年在 G20国家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虽然人们对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危机的认识有所提高,但他们对所需要的行为改变的规模仍了解甚少。
8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希望为保护和恢复自然做更多事情。然而,当被问及将采取什么行动时,大多数人表示优先考虑的事项包括增加废品回收利用和避免过度包装,而改变饮食习惯、减少使用燃油车和乘坐飞机等对气候影响更大的行为变化则甚少提及。
尽管挑战巨大,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气候临界点的莱顿并没有陷入悲观。“我的个人哲学是,把自己看作是整个地球生物系统的一部分。气候危机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学习与大自然合作,而不是与之对抗的过程。”莱顿说。
他补充道,“我认为另一个原因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们,他们让我对未来担忧,但是也给了我最大的希望。”